欧意交易所 ouyijiaoyisuo 分类>>
欧意交易所- OKX欧易数字货币交易所齐泽克:赛博空间是体验真实界的方式
欧意交易所,欧意,欧意交易平台,欧意注册,欧意靠谱吗,欧意APP下载,欧易交易所官网,欧易下载,欧易下载链接,欧易apk下载,欧易网页版,欧易交易所,欧易下载,欧易官网,okx官网,欧易客户端下载斗争。然而,他们也隐隐地意识到主体是激进否定性,死亡驱力等——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攸关之处。对真实界的构成性居间(intermediate)维度的抵抗几乎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结构,这个居间维度既非自然亦非文化,而是裂缝本身:原初疯狂、原初收缩的裂缝。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抵抗的终极境界是抵抗生命不能承受之溢出,这种溢出恰恰就是主体。消灭主体意味着试图消灭这种令人发痒/敏感的溢出,尽管如此,这种溢出是文化诞生的一种先验条件:主体作为一种故障或失灵,是自然和文化之间必要的消隐的中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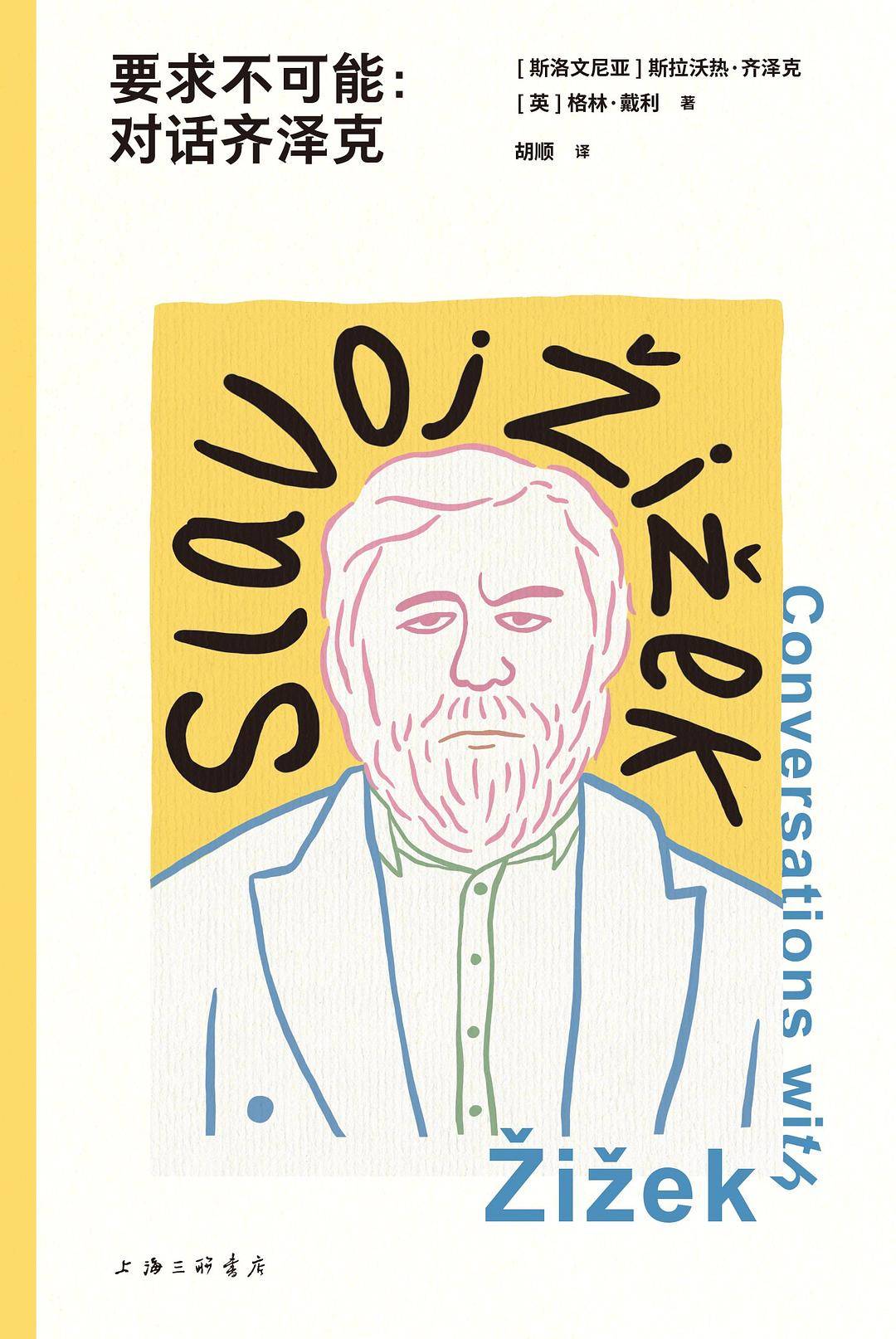
齐泽克:德勒兹的问题在于,在他的著作中,有两种逻辑、两种概念上的对立。这种对立太明显了——几乎就是法国人所说的常识——如果大家还不知道这种对立,那就太让人惊讶了。一方面是谢林式的逻辑,它把虚拟和现实对立起来:现实空间(当下的实际行为,经历的现实,以及作为人的主体,形成的个体)伴随着虚拟阴影(原初现实的领域、多重奇点、非个人因素,其随后综合到我们的现实经验中)。这就是德勒兹的“先验经验主义”(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1],德勒兹对康德的先验主义进行了独特的重塑:恰当的先验空间是多重奇异潜能的虚拟空间,是“纯粹”非个人的奇异姿态、情感和感知的虚拟空间,而且它们还不是一个前实存的、稳定的和自我同一性的主体的姿态—情感—感知。比如说,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会赞美电影艺术:电影艺术将凝视、图像、动作以及最终的时间本身从它们既定主体中“解放”出来——当我们看电影时,我们从“机械的”摄像机的角度看到图像的流动,这个角度不属于任何主体;通过蒙太奇(montage)艺术,动作也从既定主体或客体中抽象/解放出来,它是非个人的动作,然后才会归属于某个具体的人。
在生成与存在对立的标题下,德勒兹似乎糅合了这些根本不相容的逻辑——人们很容易把推动他走向第二种逻辑的“坏”影响归咎于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德勒兹本身的发展逻辑体现在早期伟大的著作中,《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和《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以及一些较短的介绍性著作,如《普鲁斯特与符号》(Proust and the Signs)和《马索克主义》(Introduction to Sacher-Masoch);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两部电影书籍标志着《意义的逻辑》主题的回归。我们要把德勒兹的这一系列著作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合写的著作区别开来,遗憾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学术界对德勒兹的接受,以及对德勒兹的政治思想的研究,其实主要是“瓜塔里化”的德勒兹:关键是要注意,德勒兹自己写的所有书完全没有直接涉及到政治——德勒兹本人就是一位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精英主义作家。因此,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什么样的内在僵局导致德勒兹转向瓜塔里。《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可以说是德勒兹最差的一本书,这本书难道不是通过简化的“扁平”方案逃避僵局之全面对抗的结果吗?这不就类似于谢林通过转向肯定与否定哲学的二元性来逃避《世界时代》(Weltalter)计划中的僵局吗?或类似于哈贝马斯通过转向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元性来逃避启蒙辩证法的僵局吗?我们的任务是再次面对这一僵局。
本身就是(意义)生成的纯粹流动产物。要么无限的虚拟领域是相互作用的身体的非物质效应,要么身体本身从这个虚拟领域中出现,现实化自己。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自己在现实的两种可能起源的伪装下提出了这个对立:形式的起源(作为生成的纯粹流动,从非个人意识的内在性中出现的现实)被真正的起源所补充,这解释了非物质的事件—表面本身从身体的相互作用中出现。有时,当德勒兹遵循第一条道路时,他会危险地接近“经验批判主义”(empiriocriticist)公式:原初事实是经验的纯粹流动,不属于任何主体,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主体和客体,作为所有固定的实体,只是这种流动的次要“凝固”。

我觉着,人们不应该对得出极端激进的结论感到恐惧。一方面,人们应该放弃这种老式的人道主义观念,即无论如何人类的尊严都会得到维护或强调。这不过是在欺骗自己。这种老式的人道主义观点教条地认为,人这个基本概念不管怎样都将在所有社会技术的变革中保留下来。但我也不认同那些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受到某种父权结构的制约,基因操控的前景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可塑性,一种新的自由。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我确信的是,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关于人的地位/定义就会改变。甚至最基本的东西,如言说、语言、情感等都会受到影响。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乐观或悲观都无关紧要。
齐泽克: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克隆本身,而在于与那些不能被克隆的东西之间的对抗。随着克隆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关于双重人的所有传统悖论。让我们举一个有关克隆的典型场景吧:父母有一个孩子去世了,他们就想要复制一个一样的孩子。但我认为这个场景实际上是骇人听闻的。有了这个克隆人,你就有了一个长相、说话、行为都和死去的那个孩子一模一样的人,但你知道,就这个克隆人而言,他或她不会是你从前的那个孩子。我想,第二个孩子是对第一个孩子的恐怖替代:与双重人最纯粹的相遇。这就像喜剧组合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老笑话,在《歌声俪影》(A Night at the Opera)的开头,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在勾引一个有姿色的小寡妇,他说:“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了你……除了你自己!”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克隆和生物遗传学的前景都让我们面临着根本的哲学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迫面对这些哲学问题。
齐泽克:首先,我认为虚拟化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数字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我认为虚拟化首先就体现了黑格尔的哲学。这并不是说我们之前处于现实之中,现在我们处于虚拟现实之中,而是说我们回溯性地知道了从未有过直接(或无中介)体验意义上的“现实”。回溯性地看,虚拟化使我们意识到,符号世界本身总是已经是最低程度地虚拟的,因为一整套符号预设规定了我们对现实的体验。我们并不会直接地体验现实,正因为如此,真实界,尤其是原初真实界(raw Real),被体验为幽灵和幻想,即那些无法融入到现实中的东西。
如果我们将虚拟现实与实际现实(realreality)进行比较,那么真实界不应该被视为实际现实中无法被虚拟化的部分。为了实现虚拟化,我们必须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现实的虚拟化究竟是如何实现的?虚拟化空间如何从现实本身中显露出来?唯一符合的答案是,现实本身,用拉康的术语说,就是“并非—全部”(not-all);在现实本身中,存在一道裂缝,而幻象恰恰填补了现实中的这道裂缝。虚拟化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真实界在现实中凿开了一道裂缝,然后由虚拟化填补这道裂缝。
齐泽克:我甚至想说,这种真实界的概念与量子物理学中宇宙思辨的结果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在这种宇宙思辨中,你也会认为,宇宙就其整体而观之是一个空无。这就是德勒兹所说的普遍化透视主义(universalized perspectivism)的唯物主义立场。这并不意味着既然一切都是主体的视角,那就没有现实了;普遍化透视主义比这更激进。如果我们从特定视角去认识事物,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种认识是对事物本身的一种扭曲的认识。但普遍化透视主义得出了更激进的结论,如果你拿走这个扭曲的视角,你就会失去事物本身。现实本身就是某种扭曲视角的产物。
在这些扭曲之外,没有积极的现实。这个洞见——我的天呐,我这里的口吻快要成一个新福音派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在作为大乘(Mahayana)佛教创始人的龙树(Nagarjuna)菩萨那里看到。龙树菩萨认为,佛教所强调的空无的概念,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空无。相反,佛教认为,每一个积极的实体都涌现自一个扭曲的视角,没有什么可以客观或独立于这个视角而存在。从客观上说,无物存在,实体只是作为透视的差异化之结果涌现出来的,而每一种差异化又无非是部分的扭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co-Criticism)一书中是如何试着做一名唯物主义者的:他对反映外部客观现实的意识概念很着迷。然而,这种意识概念依赖于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因为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反映之外,有客观现实)预设了反映现实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于这种现实的凝视。普遍化透视主义拒绝任何这样的凝视。关键不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没有现实,而是在现实之外没有意识。现实的扭曲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意识是现实的一部分。因此,当列宁强调,我们只能在一个无穷渐进的近似过程中达到客观现实时,他忽略了我们的现实的扭曲恰恰是因为我们是现实的一部分,因此对现实不能持一种中立的立场:我们的感知扭曲了现实,因为观察者是被观察对象的一部分。我认为,正是这种普遍化透视主义包含了一种激进的唯物主义立场。
唯物主义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在我们对现实的扭曲感知之外,还有一些本体的(noumenal)现实。唯一一致的唯物主义立场是,在康德的意义上说,作为一个自我封闭之整体的世界并不存在。作为一个积极的宇宙,世界预设了一个外部的观察者,一个不被困在其中的观察者。你把世界视为一个自我封闭之整体的位置恰恰是一个外部观察者的位置。因此,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激进的透视主义使我们能够形成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立场,不是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而是我们的意识不存在于世界之外。列宁把重点放错了。唯物主义的问题不是“现实存在于意识的外部吗?”,而是“我们的意识存在吗?”“我们的意识如何存在?”“意识如何是现实所内在固有的?”

齐泽克:以疼痛为例。现实的虚拟化和无穷无尽的身体疼痛(这种疼痛比通常的疼痛要剧烈得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难道生物遗传学和虚拟现实的结合不是增加了受疼痛折磨的“增强版本的”新可能了吗?不是为拓展我们忍受疼痛的能力开辟了闻所未闻的新视野吗(通过增强我们忍受疼痛的感觉能力,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直接攻击大脑中心,绕过感官知觉,从而发明新的疼痛形式)?也许那种终极萨德式的“不死”的疼痛受难者形象会变成现实,这种受难者可以忍受无尽的疼痛而不能选择通过死亡来逃避。在这样一种情形中,终极的实际/不可能的疼痛不再是实际身体上的疼痛,而是我在其中运动的虚拟现实所引起的“绝对的”虚拟—实际疼痛(当然,性高潮也是如此)。直接操控我们神经元的前景开辟了一种更“实际”的方法:虽然这种痛苦的“真实”不是作为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的一部分的那种真实,但它是不可能—实际。同样的说法不也适用于情绪吗?回想一下希区柯克关于直接操控情绪的梦想:在未来,为了在观众心中激起恰当的情绪反应,导演不再需要构思复杂的叙事,不用再以令人心碎的方式把它们拍出来;用一个直接连接到观众大脑的小键盘,这样,当导演按下相应的按钮时,观众就会体验到悲伤、恐怖、同情和害怕等情绪——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到这些情绪,这种情绪体验是“实际生活中”引起的害怕或悲伤等情绪体验所无法比拟的。特别重要的是,将这一过程与虚拟现实区分开来:恐惧不是通过能够引起恐惧的虚拟图像和声音产生的,而是通过直接干预产生的,完全绕过了感知层面。这不是从人造的虚拟环境中“回归实际生活”,而是由彻底的虚拟化本身产生的真实界。因此,我们在这里体验到的是最纯粹意义上的现实与真实界之间的裂缝:真实界,比如说直接干预神经元产生的性快感,并不发生在身体接触的现实中,但它“比现实更实际”,更强烈。因此,这种真实界破坏了现实中的对象与其虚拟拟像
因此,根本上来说,赛博空间是模棱两可的。它既可以作为一个阻挡真实界的中介、一个没有障碍的想象空间的中介,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你可以接近真实界的空间,它的排斥对你的社会现实体验来说是构成性的。赛博空间既是一种躲避创伤的方式,也是一种形成创伤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瓦格纳的《帕西法尔》(Parsifal)中的悖论一样,即矛伤还得矛来治/解铃还须系铃人。一方面,赛博空间会使人陷入到一种想象的内部循环运动危险中,但另一方面,赛博空间打开了一个与真实界遭遇的空间,正是我所说的想象的真实界:也就是幻象的真实界,这个我们在现实中无法阻止的创伤性维度。赛博空间是体验真实界的方式
比如说,在赛博空间里,与真实界的可能遭遇会是某种幻象的构造,这种幻象本身是如此极端,以至于你会愿意逃回“实际生活”。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弗洛伊德的病例中,一位父亲梦见他的儿子在责备他:“你没看到我被火烧到了吗?”为了避免这种创伤性的遭遇,这位父亲接着逃回到清醒的生活中。在赛博空间中,我们总是有可能接近我们幻象空间的基本架构。但是,正如拉康指出的,基本的幻象是无法承受的;无法忍受的意思是,一个人永远无法将这些幻象完全主体化,整合进自身之中。因此,真实界不仅仅是符号化的外部界限,它完全是内在固有的:符号化自身产生的裂隙。在这个意义上说,与符号秩序相关,真实界也有一种近乎易脆的特征。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区分我所赞同的宗教意识的回归(这也可以在巴迪欧、阿甘本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找到)与晚期解构主义者列维纳斯—德里达式的关于宗教回归的观点。在列维纳斯和晚期解构主义者那里,宗教回归意味着我们意识到了激进的他者性,以及感受到了对他者性无条件的开放和责任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所说的宗教回归更关注的是具有英雄色彩的决断主义(decisionism)(我们不应该害怕使用这个词)。这种决断主义很强调在实际处境中采取冒险的后果并为之承担责任。回到死刑的例子,那些宣称反对死刑的人缄默地预设了世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齐泽克:在这里,我是一个坚守传统伦理的人。我认为有些东西,比如荣誉、羞耻、自由等等,都是值得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人的生命从来就不仅仅是生命本身。人的生命之中一定蕴含着某种特定的溢出,人可以以生命为代价来追寻这种溢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恢复永恒、决心、勇气和英雄主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在这件事上,我完全同意巴迪欧的观点。我跟你说,在我和巴迪欧的一次谈话中,当我们谈论我们的个人爱好时,让我非常惊讶和满意的是,他也非常喜欢美国的西部片。你怎么也想不到巴迪欧,这样一位现代的马拉美(Mallarmé)、亲法、据说反美的学者,也会喜爱美国的西部片。当我问他为什么喜爱时,他跟我说,美国的西部片是唯一关注勇气的电影类型。
现在如果我们以今天这类型的电影,那就是战争电影了。比如,在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中,你可以看到无尽的恐怖、毫无意义的屠杀和暴力。斯皮尔伯格的视角也是一种末人的视角:也就是说,战争只是一场噩梦,一种令人难以理解、可悲的人类生命的消耗。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诺曼底登陆中,既有渴望胜利目的的英雄主义和伦理斗争,也有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和理想。顺便说一句,这也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一种主导性趋势,即把那些准备为某种事业或目的而献身的人说成是盲目的狂热分子。
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西部片遭遇了危机,一部分原因可以说是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导致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所谓的元西部片,融合了其他类型的电影。尽管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部片还是出现了短暂的复兴。虽然这些影片反映了某种忧郁的怀旧态度,但它们还是挺棒的。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当然是《正午》(High Noon),尽管它不是最好的,但它体现了巴迪欧所说的西部片的精神主旨:勇气。但我认为,另外两部电影在这个系列中更为重要,它们是我最喜爱的西部片。这些不是人们通常提到的安东尼·曼(Anthony Mann)的电影,而是德尔默·戴夫斯(Delmer Daves)的电影:《决战尤马镇》(3:10 to Yuma)和《吊树》(The Hanging Tree)。这两部电影都是关于伦理磨难、勇气和危险的:你会为了什么而不顾一切危险?这通常是西部片关注的焦点问题——你在哪一个关键时刻会鼓起勇气去冒险?
齐泽克:绝对是。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是重点。是的,“风险社会”这个术语不适合来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里没有选择。即使有很多风险,那也是被动的风险。对我来说,这就是风险社会的基本悖论。比如说,让我们以最近安然和世通公司的破产为例。我的意思是,仅仅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破产事件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失业的贫困员工并没有冒任何风险。他们所经历的纯粹是很荒诞的命运。我认为,当风险社会理论家用“你今天可以自由选择,可以任意冒险”之类的话语给我们洗脑时,他们的观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像老式的意识形态那样,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荒诞命运解释为我们的风险选择。看一下安然公司或世通公司中的这些中层员工,他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的毕生积蓄等等。那他们又做了什么选择?他是否有理性的方法来证明为什么安然或世通公司应该倒闭,而不是其他大公司?在这里,风险被绝对地客观化为一种匿名的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2026-01-07 19:16:31
2026-01-07 19:16:31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